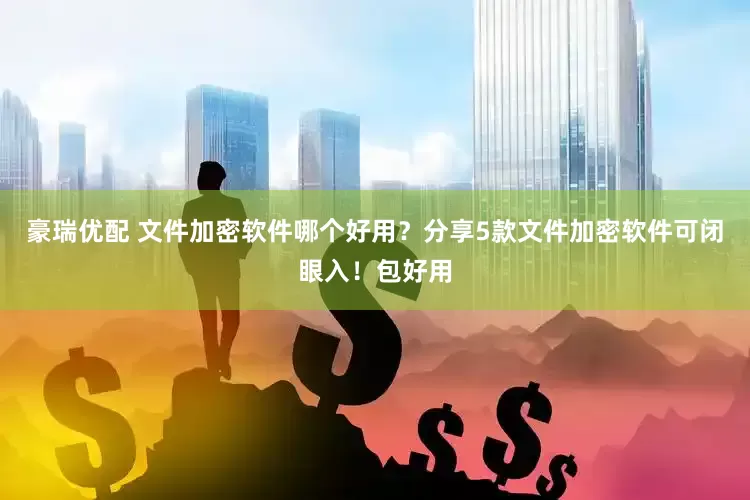湖南雨花非遗馆,已成外地客人到湘旅行的打卡地。我去过非遗馆很多次,看到那些熟识的旧物,总会想起旧日时光。
过去乡间家家户户都有石磨,那些磨盘如今都铺在一些园子的路上,用来装点古意。雨花非遗馆的石磨依然在磨坊转动,常有年轻父母领着小孩子去,告诉孩子们这是做什么用的。那些年轻父母也都是没有推过磨的,看着他们推磨动作不在行,我忍不住充里手,说:“快碓慢磨,意思是舂碓要快,推磨要慢。”年轻父母们没见过石碓,脸上更茫然了。
记得小时候,我家的磨子放在中堂屋。我人小,力气不大,通常是同二姐一起做事,推磨也是我俩一起推。磨糯米做重阳糍粑,磨籼米粳米做米糕。我没有二姐勤快,只想快快磨完,好跑出去玩,二姐就告状:“奶奶,六坨不是推磨,他在拉!”此处“拉”读作第三声,也是一种推磨法。比如玉米磨成细粉很不容易,就得先“拉”一回,磨成小颗粒,再去磨成细粉。倘若做粉碴肉,米粉不需太细,只“拉”一次就行了,就得推快磨。
我在雨花非遗馆见到一个直径一米多的石磨,疑心它是摆样的。磨子没有这么大的,手力推不动。创始人郭存勇先生颇有几分得意,说:“我设计的电动磨子,改良版的,可快可慢。”听他这么一说,我倒想起水车咿呀的老磨坊了。过去乡下,有落水潭的地方,通常可见水车磨坊。磨坊必定有碾子,磨坊也叫作碾坊。奶奶说,旧时候殷实人家才挑着谷子到碾坊去,升斗之家的米是餐擂餐的。说的是穷人家没那么多的谷子,每天撮几升谷放在石碓里擂。
图/微信公共图片库天津配资大本营
郭存勇先生站在一个五金匠人挑担前,很有兴致地解说:这个是坩埚,那是风箱。我们老家,把五金匠人都喊作补锅匠,其实他们修锁、修伞、修脸盆,样样都做。补锅匠进村响动大,一串铜板叮叮当当地甩着。
妈妈便出门喊:补锅匠!补锅匠!补锅匠的担子,一头是风箱坩埚,一头是装些碎铁块破铁锅的木箱或圆底竹箕。风箱一拉,火苗猎猎,坩埚里铁水熔了。补锅匠进村,孩子们都围着看稀奇。
非遗馆的老纺车和老织布机,最能勾起我的童年记忆。我是在纺车和织布机边长大的。我家乡喊织布机作床机。旧时候,乡下人身上穿的,床上盖的,都从纺车和床机上出来。
奶奶和妈妈纺纱织布在村里是闻名的,常有女人上门请教各种花样布的织法。蚕丝掺在染青的棉纱里,织出的布喊作金纱布,那是最好的汗衣料子。我乡下喊衬衣作汗衣。男人夏天出门做客,穿一件对襟盘扣金纱布汗衣,坐下来卷喇叭筒烟,腰都挺得直些。
弟弟四岁时,眼睛不慎受了伤。送去县医院治,不见效,医生建议我父母把弟弟送到邵阳医院去。家里已拿不出钱了,妈妈一拍手,说:“被子铺盖全部卖掉!”妈妈把全家的被面、蚊帐都从床上撤下来,又清出些当季不穿的衣服,挑到集市上卖掉了。
爸爸带着我弟弟去邵阳治眼伤,妈妈在家隆日隆夜纺纱织布。盖没有被面的被子,我老家人喊作盖毛絮被。一家人盖了一个月毛絮被,爸爸领着我弟弟回家了。爸爸很惊讶,他见家里每个房间的床上都换上了新被面、新蚊帐。村里的女人都到我家里来看热闹,夸我妈妈是织女仙姑。
人是不可能走出故乡的,哪怕他走过了万水千山。非遗馆的那些旧宝贝,寄托着我们的精神原乡。
原文首发于《时代邮刊》第485期
2025年6月·新中年
编辑/王雅娜
编 辑 | 胡晨曦 审 核 | 李 玲 终 审 | 黄 菲天盛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